中华读书报:热情的支持,谆谆的教诲——追忆叶圣陶先生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作为一名普通的语文教师和叶圣陶先生结识,书信往还,并面聆他老人家的教诲,受益良多、终生难忘。
那是1978年以后,改革开放的大潮兴起。我在北京外国语学院(今北京外国语大学)附属学校担任语文教学工作。学校得风气之先,进口了一些国家的母语学习教科书。我和北外的几位教师自发组成了一个国外语文教育研究小组,把这些教科书和资料翻译整理,写成文章,发表在当时的语文刊物上,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叶圣陶先生是语文教学界最受人尊敬的老前辈,因此很想听听他的意见。1980年1月,我们给他老人家写了一封信,请他指教。很快就接到了他的亲笔回信。他在信中表示,很赞成我们做的事,“虽然没有见过面,已经是心心相通的朋友了”。并指导说:“外国语文跟我国语文完全不同,可就教语文和编辑语文课本的目的和方法而言,不妨看看外国人是怎么考虑的。看看当然不是照抄,拿来做借鉴却是有好处的。”叶圣陶先生站在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高度,支持我们的研究工作,使我们深受鼓舞。
1980年11月,我受教育部和人民教育出版社邀请,参加了全国第二次中学语文教材改革会议,在会上报告了国外语文教学的情况,提出了一个新的语文教材的编写方案。我的方案是:以系统培养学生听说读写能力和学习一定的语言知识为目的,编排阅读、写作、听说、语言知识等四种课文。从纵的方面看,各种课文自成体系,分别培养学生各种语言能力;从横的方面看,各类课文相互配合,提高学生综合运用的能力。我把方案寄给了叶圣陶先生征求意见。他老人家给我回信,对我设计的方案表示赞同。特别对听说教学做了具体指导:“作听人讲话的笔录或摘要来练习听,举办讲演会、辩论会来练习说。平时要注意听和说,无论在校内校外,同学互勉,师生互勉。”还表示:“课文都要站得住,没有病句,没有空泛的话。四种教材都要如此。这一层最难办到。”
在叶圣陶先生的鼓励支持下,1981年到1984年我参加了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初中语文读写分科实验课本的编写工作。1986年到1988年又参加了人教社从初中到高中通用语文教科书的修订、编写工作。负责从初中到高中教材中听说教学的整体设计和教材的编写。
除此之外,我还追随叶圣陶先生,参加了一些语文方面的学术活动。在北京语言学会举办的“礼貌和礼貌语言”座谈会上,叶圣陶先生到会做了《诚于中而形于外》的讲话,并给《礼貌和礼貌语言》一书主要编写者的我写信,发表了具体的意见。他老人家还亲手批改我参加编写的《实用语言浅说》一书的书稿;从遣词造句,到标点符号,既做批改,又做说明分析,令我万分感激,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老人家还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在东四十条的寓所接见我,就语文教学方法、教材编写、语文教学史研究等问题与我深谈。
叶圣陶先生一生,从教育兴国、民族复兴的理想出发,始终关心着儿童、青少年的语文教育工作。从民国到新中国成立,他身体力行,编写了多种语文教科书;办杂志,出专著,成了一位伟大的语文教育家。出于这种事业心,对像我这样改革开放后冒出来的热心语文教育的新人,给予了超乎寻常的鼓励和支持。叶圣陶先生高尚的道德品质,博大精深的语文教育思想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我终生在语文教育领域上深耕:编写国内中小学生和国外汉语学习者使用的语文教材和指导书;秉承他老人家严谨的治学精神,潜心研究,出版汉语与中国文化、语言对比分析、汉语教育史等方面的专著。在北外的本科和研究生教育中,我常在今天的一代新人中,宣扬学习叶圣陶先生爱祖国、爱人民,脚踏实地、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专业领域勇做贡献的精神。我认为,传承叶圣陶先生这种精神,是我们对他老人家诞辰130周年最好的纪念。
(本文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中文学院原副院长、教授鲁宝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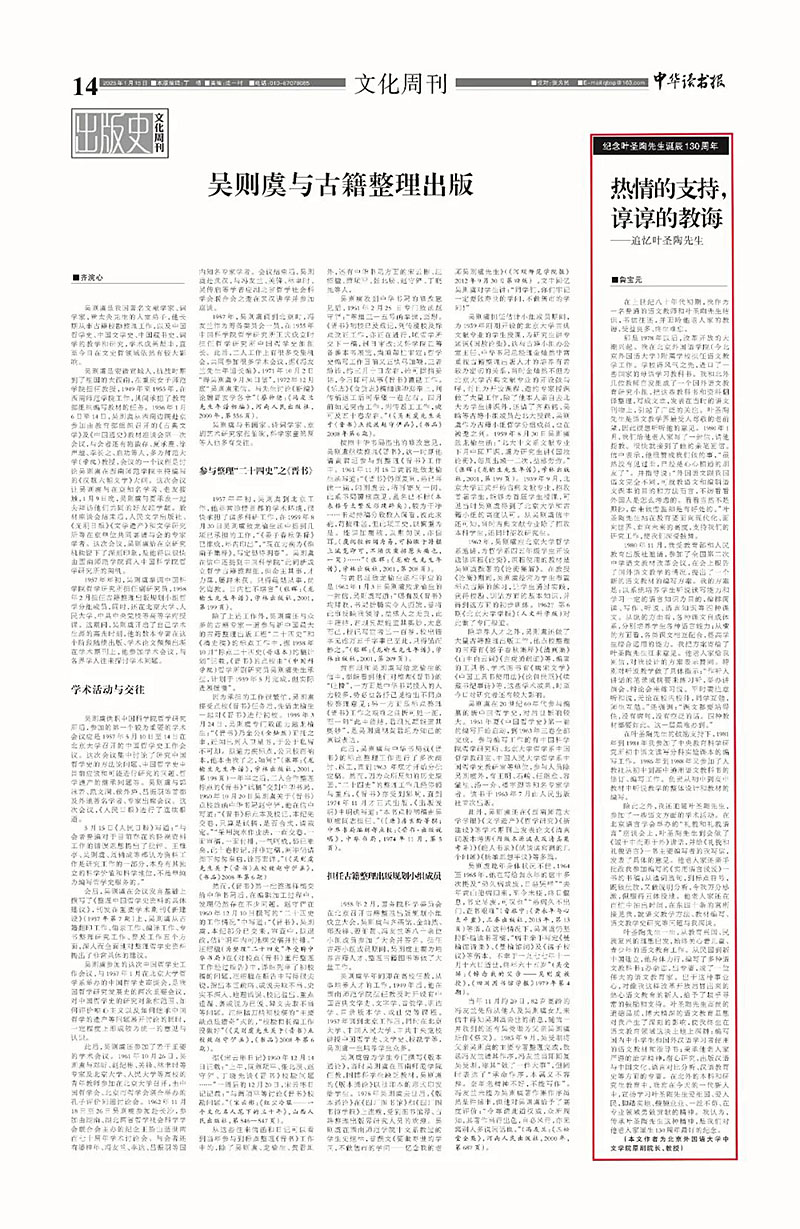
文章转载自《中华读书报》2025年1月15日第1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