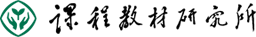摘要:作为一种信息时代的课程形态,微课程借助信息、数字与媒体等现代技术,业已引发了传统课程生态系统的连锁式变革。它在汰变更新传统课程的物质载体、传播渠道、呈现方式与教学模式的同时,更迭代创生了不同以往的知识形态、人知关系、认知结构与习得机制,为我们呈现了一幅知识形态的“网络化”、知识表达的“可视化”与知识习得的“具身化”图景。透视微课程视界中知识样态的上述表征,既有益于对教育信息化深入课程软腹地带作出前瞻的理论探寻,也有益于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论辩可能的实践路向。
关键词:微课程;知识样态;知识表达;知识习得;时代表征
中图分类号:G423.04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1298(2016)01-0029-07DOI:10.14082/j。cnki。1673-1298.2016。01.004
总体上讲,人类教育的发展史其实就是知识传播的技术介入并影响教育的历史。无论在文字的产生与应用的早前阶段,抑或是在造纸与印刷技术的勃兴时代,还是在电子与视听技术席卷裹挟的晚近以降,课程知识的变迁可以说须臾未曾离开过技术的融入与形塑。尤其在当下,以迅猛发展的信息、媒体与数字技术为支撑,传统课程知识的理解方式、呈现形态、传播渠道与教学方式等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激变。与此种情势相对应,以短小精湛、主题突出、易于扩充,适切翻转学习、混合学习、移动学习等为特质的微课程一经出现,便迅速引起了人们的密切关注并付诸实践,业已引发了传统课程生态系统的连锁式变革。站在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的交叉路口,我们有必要探析以下问题:作为信息时代孕育的一种新型课程,微课程视界中的知识存在形态发生了怎样的时代变迁?亘古未易的知识表达方式发生了怎样的汰变更新?历史绵延的知识习得模式又发生了怎样的新陈代谢?毋庸置疑,对这些问题的应答,既有益于对教育信息化深入课程软腹地带做出前瞻的理论探寻,也有益于为信息技术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论辩可能的实践路向。
一、知识形态的“网络化”
知识的“网络化”这一命题由美国学者戴维?温伯格(DavidWeinberger)提出,他在反思信息时代知识形态的著作《知识的边界》中认为,在信息超载的当下,知识在网络中产生,也在网络中跳转,已变成网络的一种属性。作为一种开放流动的交互性存在,知识不再存在于书籍之中,不再存在于人的头脑之中,而是存在于网络本身。在他看来,传统上状如书籍的知识是“长形式”的,而信息时代的知识则是“网形式”的:“如果你想写一本书,你就不得不与自己对话,想象各种可能的反对观点,因为书是一种与读者相分离的、非对话的、单向度的媒介。我们不得不依赖这种自言自语,但并非思想本就是如此,而是书将知识固定在了纸上。我们不得不建立一个长长的思想序列,由一个想法通向另一个想法,只是因为书籍是一张张纸装订起来的。‘长形式’思考之所以看起来如此,是因为书籍将它塑造成这个样子。而且,因为书一直是知识的媒介,所以我们就认为,知识就应该是那个样子的”[1]185-187。而如今,知识终于拥有了一种能够帮助它超越这种局限的媒介———网络。在网络中,知识具有更强的流动性、更高的联通性以及更好的交互性,它正在对知识的本质以及“长形式”思考在其中发挥的作用带来一些根本性变化:“如果我们将知识视为孤立的内容,而不去联系它所处的那种新的、超链接式的对话、争辩、阐释甚至对骂的上下文,那么我们就错失了知识正在经历的最重要的变化,知识现在不再是那个孤独的作者坐在自家舒服的椅子上传递给读者的内容,也不再是站在教室前面的教师给那些坐在不怎么舒服的椅子上的学生传递的内容……而是存在于一张细密杂乱的大网之中,正如生命并非活在我们的神经、骨骼、血液、骨髓之中,而是活在这一切所构成的联系之中”;概而言之,“如果‘长形式’的书籍告诉我们,知识是从A到Z的漫长旅程,那么网络化的知识可能会告诉我们,世界并非是一个逻辑严密的论证,而更像是一个无定形的、相互交织的、不可掌控的大网”。[1]151-152此种关于知识网络化的见地,为我们理解微课程的知识形态洞开了新的视界。
迄今为止,关于微课程的知识形态,人们往往浅表地认为,微课程短小精湛的特点,决定了它必然同时具有孤立、零碎、割裂等致命弱点,利用微课程进行学习,学到的知识必然会零碎、割裂、不成体系。[2]固然,单个、孤立的微课程将知识点进行切割、碎化,形成信息孤岛,确实无法实现知识的联结、整合与贯通。然而,从课程论上看,这既不符合人类的认知规律,也不是知识的本然结构,更不应成为微课程存在的旨趣。笔者以为,微课程的“微”并不等于知识点的“碎”,对知识加以“碎片化”处理,只是突破传统教学中重难点、易错点、混淆点的环节或手段,其终极目标是在知识点之间建立非线性但相关联的“知识网”,亦即使知识以“网络化”的形态来呈现。当然,这里知识的网络化,包含“知识本身结构的网络化”与“知识传播路径的网络化”两层含义。
关于知识本身结构的网络化,笔者已撰文阐述,微课程对知识的处理是沿着“知识切割—脉络联结—系统整合”的线索来展开的:[3]首先,是科学萃取知识点。即从缜密的知识体系出发,精准析出、提炼、萃取出重难点、易错点、易混点,同时清晰呈现它们之间的内在关联。如此一来,每个知识点就能唤醒先前的认知经验,继而又可引出后续的知识单元。其次,是梳理知识点脉络。如前所述,以知识点之间的逻辑关系为“线”,将若干既相对独立又彼此相关的知识点进行关联化、序列化、体系化处理,这样就能够形成网状结构的知识点脉络。如果再把这个脉络放大,就会发现大知识点周围还联结着若干小的知识点,学习者只要贯通知识点之间的学习脉络,就可避免所学知识的碎片化与彼此孤立。[4]最后,是建构数字化知识网。如果说人类知识是以学科为“纲”、以课程为“目”编织而成的“网”的话,那么纽结于“纲目”之中的若干“网节”就是以小粒度或小模块形式存在的“知识点”。而在教育信息化的视野下,我们借助网络、媒体与数字技术,对星罗棋布的知识点加以挖掘并以微视频方式呈现的“微课程群”,也就构成了一张纲举目张的数字化“知识网”。
就知识传播路径的网络化而言,微课程的知识教学本质上也是一种“网络化”过程。较之传统课程,介入网络时空的微课程的传播已不再沿袭传统的线性、单向与封闭路径,而是循着非线性、弥散化与开放式的脉络展开。一方面,就微课程的知识点遴选来讲,它旨在挖掘学科教材中的小粒度知识,并以微视频的形式来加以呈现。事实上,这些从学科教材中析出的知识点,已通过课程专家的筛选与教育部门的审核,而那些被排除在纸本教材以外的内容则未必就不是可传递的知识,只是它们不符合知识点的“遴选标准”而已。现如今,在微课程的实施中,那些经遴选而旁落的知识则可以微点评、微反思等形式向学生个性化推送,以强化他们对知识点的理解、内化与迁移。即是说,在网络时空中,微课程的知识点是以可还原、可增补、可更新的面貌来呈现的,它超越了传统课程里知识点的那种裁剪的、审定的、静态的呈现方式。事实上,此种差异导源于书籍与网络的区别:因为书籍的物理特性倾向于按序延展下去,而非中断分岔。与叙述的狭长小径背离的那些观点,就算再有价值,看起来也像是干扰、分散读者的注意力。书籍只是不够长,不足以让那些“长思考”自由舒展成它们本来的样子。[1]164而网络则有足够的空间,它所呈现的是边界弥散、连续不断、绵延此刻的“知识喷泉”,它既能容得下传统上多卷本的长篇大论,也会为那些完全用“推文”表达的短小观点留出位置。概而言之,在网络时空中,知识无需刻意地遴选、屏蔽或排除,“点击率”决定了它们的位置,即便是那些“无人问津”的知识也不会消失,只是被冲刷到了知识网络的边缘而已。
另一方面,就微课程的知识点建构来说,承前所述,传统课程的知识单元一经审核裁定,也就被固化为不可协商、不可修正、不可增删的“真理性”存在,而网络时空中的微课程,已将学科知识点嵌入到网络之中,使之具有了人机交互性、人际协商性与动态生成性,甚至因此改变了课程知识的建构主体与创生方式。众所周知,对于同一个学科知识点,不同主体研制的微课程,从知识挖掘到方法选择、再到呈现方式等都可能各不相同。更有甚者,在开放互动的网络中,课程专家、学科教师、学生个体、教育官员乃至社会大众均可参与微课程建构。也就是说,在这个人人都可以“出版”的时代,已没有人会被神化为某个领域唯一可靠的专家,我们正在亲历“从纸质专家知识模式向网络专家知识模式的转型”[1]104-105。笔者以为,如今,专业知识已被嵌入数字网络,并由此获得了强大的能力,它已摆脱旧媒介的规约,而拥有了新媒介的属性:其一,在纸质时代,课程知识看起来是可以分割成各种可掌控的领域;而在网络空间中,微课程的知识点不会被整齐地分割,它们弥散地存在于各种关联之中;其二,传统上课程知识随着教材的出版通常只有一次表达机会,而如今以微课程形式嵌入网络的知识点几乎是各种意见的荟萃,而且可以即时更新;其三,课程知识的建构过去是不透明的,而网络化的微课程则会附带密集的“超链接”,以便还原知识点赖以存在的情境;其四,在前网络时代,课程知识是单向传播的,教材只是“一对多”的知识媒介,而今微课程的知识传播方式已发生变化,因为网络是多向互动且富有创造性的,能够对各种观点即时做出更为积极的响应。一言以蔽之,网络是连接性的,其连接的规模、范围、透明度与多向性,已远远超越了有史以来任何媒介的性能。以此观之,栖身于网络之中,微课程的知识样态必然会烙上网络化的印记。
二、知识呈现的“可视化”
总体而言,人类对知识可视化的探索有着漫长的过去,而作为专门的研究主题却仅有短暂的历史。亚里士多德在谈到学习方式时曾说:告诉我的我会忘记,给我看的我会记住,让我参与的我会理解。我国宋代史学家郑樵在《通志》中有云:“置图于右,置书于左,索象于图,索理于书。”[5]由此可见,图画与文字互补、意象与思想交融有助于促进知识的理解。苏联教育家沙塔洛夫认为,通过形象进行思维是人的思维所固有的特点,视觉记忆是一种可靠的机制,记忆具有选择性,在脑中保存许多意义相关联的联想是人脑的一种奇特的能力。[6]我国的《蒙养图说》《字课图说》别出心裁,针对学童喜欢可视化表征世界的认知偏好,创制了化抽象为形象的教材绘本。回顾历史,可以这样说,人们对将知识转化为形象、直观、生动的图形、图表、图像,以促进知识的传播、理解、迁移与创生的探索从未停歇;审视当下,正如有论者所言:人类历史中正在发生一个重要的转变———图像的转向;[7]展望未来,借助新思维、新技术、新工具,人们必将把知识可视化推向新的高度,一个影像认知的时代必将迎面而来。
需要指出的是,与早前时代“将任何抽象的事物、过程变成图形、图像的表示都可以称为可视化”不同,在信息技术狂飙突进的当下,“知识的可视化则是在科学计算可视化、数据可视化与信息可视化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研究领域”[8],“它研究的是视觉表征在改善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之间的知识创造与传递中的应用,指所有可以用来建构和传递复杂见解的图解手段”[8],除了传达信息以外,其目标还在于传输见解、经验、态度、价值观、期望、观点、意见、预测等,概念图、思维导图、认知地图、思维地图是其常用的工具。以此来透视当下的课程,有学者基于信息技术与课堂教学融合的实际,指出知识的可视化具有形象性、自主性、陶冶性与创造性等特征,有利于促进学习者的认知发展、激发学习者的想象力、创生全新的教学时空。[9]作为一种借助信息技术的认知工具或认知方式,知识的可视化能够“帮助教师采用学生易于理解与接受的教与学的方式,激发学生的学习动机,使教师的教在学生‘想学’‘愿学’‘乐学’的心理基础上展开”[10],也能够使学生的学在自身“学会”“会学”“活学”的能力层次中升华,从而促进教与学的生动性、趣味性与有效性。
笔者以为,微课程实际上正是借助知识的可视化这一技术,才得以在当下的教育教学实践中引发传统课程生态的连锁式变革的。作为一种新的认知或学习方式,微课程的知识可视化既能改变学生学的方式,促进有意义学习与深度学习的产生,更能深化教师教的反思,辅助设计教学,将需要感知、认识、想象、推理的事物及其发展变化的形式与过程,用仿真化、虚拟化、形象化、生动化的方式呈现出来。概括地说,微课程在推动知识可视化上主要表现为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知识内容的可视化呈现。在微课程的知识教学中,教师突破了传统的“粉笔+黑板”这一单调、呆板、直白的内容呈现方式,转而依据学生的身心特点与知识经验、学科的知识类型与体量大小,综合运用听觉、视觉、触觉等多种感官,合理选择图片、动画、音频、视频等呈现方式,对碎片化的知识进行选择、挖掘、组合与联通,使之融合为富有特定意义的信息模块,以促进知识形象、直观、生动、高效地传递、理解、内化与迁移,进而在课程知识的呈现方式上实现了从单调、机械、直白向丰富、灵活、多维的转向。举例来说,在地理科学中,气压的变化、地质的分布等现象无法直接观察,可以绘制知识草图来加以呈现,从而给人以直观的印象;在化学教学中,分子结构、化学反应等知识讲解较为抽象,可以利用可视化技术进行演示,以加深学生的知识理解;在物理实验中,电磁场、核辐射等现象肉眼无法观察,可以用虚拟仿真的视频来展演,以获得常规实验无法达到的效果,同时也避免了可能发生的危险。
第二,教学方式的可视化表达。较之传统课程教学采取以教师、教材、教室为中心的教学方式,遵循以学生课前预习、教师课堂讲授、训练课后完成的先教后学、以教定学、教主学辅的授受流程,微课程的勃兴与实践业已实现了从教学理念到教学方式、再到教学流程的翻转,逐渐形成了先学后教、以学定教、学主教辅的范式转向。在时下的翻转课堂中,微课程的知识教学依托信息技术与网络时空,将传统课堂中的“课上”讲授活动转变为“课下”的自主学习,使得教师作为课堂上的“主演”退居为知识教学的“导演”,学生作为知识灌输的“容器”跃升为知识学习的“主体”。不可否认,支撑这种教与学方式翻转的,正是知识可视化技术的应用以及由其引发的教与学时空的分离。
第三,学习情境的可视化体验。在后现代知识观看来,知识从来就不是静态的、机械的、僵死的,它是情景化的、可体验的、生成性的。因此,情境的还原、复演、创设与感知对于丰富儿童的“认知经验”与“情境履历”至关重要;而对于这两者割裂的教育危害正如杜威所言:“一是平常的经验难以得到丰富,这种经验并不因为学习而更加丰富;二是因为学生习惯于一知半解和生吞活剥的教材,把这种教材装到脑子里去,这种态度便削弱思想的活力和效率”。[11]在教学中,如果我们希望培养学生对知识的自主学习与体悟能力,那么以微课程的形式向他们提供诸如图像文本、电脑课件、录音录像与短小视频等丰富的可视化资源,积极创设当前学习主题与视觉信息文本耦合的学习情境就显得极其必要。比如,执教《雾凇》一文,如果教师首先鼓励学生反复诵读来探寻雾凇的成因,接着引导学生划出并按逻辑顺序串联课文中的关键词,进而在学生头脑中想象一幅雾凇图,最后再用微课程来演示松花江畔千姿百态的雾凇景观,那么就能通过优美的语言、形象的画面、流动的图像,带领学生融入文本、融入自然,从而获得独特的情境体验。
第四,问题解决的可视化实现。美国学者埃德加?戴尔(EdgarDale)的“学习金字塔”表明,不同的学习方法达到的学习效果不同,初次学习两周之后的知识保持率由低到高的次序为:阅读、听讲、视听、演示、讨论、实作、互教。即,在众多的学习方式中,单独调动一种感官进行学习,效果会在较低的水平上徘徊,而综合运用眼、耳、口、手、脑等器官展开的问题解决式学习,则能够取得较高的学习效能。也有实验表明,解决问题与知识建构是双向强化的。[12]因为知识建构的实现必然以问题的解决为基础,而问题的解决也必然要求综合运用各种知识,所以通过解决问题来强化学习是一种有效的学习模式。然而,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问题的解决,还是知识的建构,都是较为复杂且难以具现的认知过程,传统的知识传递方式既无法观测更无法呈现,而微课程则能够以可视化的方式轻松完成。比如,在化学实验中,化学反应的发生常常在顷刻间完成,电子在原子核间的跳转往往在转瞬间消逝。对于这些人眼无法窥探的过程,现在通过虚拟的网络视频已能清晰呈现出连贯的、细微的步骤。正是因为创立了复杂化学系统的多尺度模型,马丁?卡普拉斯(MartinKarplus)、迈克尔?莱维特(MichaelLev-itt)与阿里耶?瓦谢勒(AriehWarshel)才获得了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这表明,问题解决的可视化已闯进我们的课程知识领地,它借助过去难以企及的数字化、仿真化与可视化技术,使我们获得了身临实境的认知体验。
三、知识习得的“具身化”
20世纪80年代以前,具身认知仅是一种哲学思潮,后来逐渐走向实证领域,目前已转向自然情境下的认知研究。在现象学的视界里,梅洛?庞蒂(M。Merleau-Ponty)认为,身体是知觉的“主体”,而非被认识的“客体”,认识过程实质上是身体的表现,身体是我们与世界关联的中介。[13]在生物学的论域内,贝特森(G。Bateson)与瓦雷拉(F。J。Varela)强调,认知依赖主体经验的种类,而这些经验乃是出自于具有各种感觉运动能力的身体;人的感觉运动能力本身根植于或嵌入于一个更加广泛的生物的、心理的和文化的情境中。[14]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奈瑟(Neisser)与西蒙(Simon)则主张,以生态学的方法取代此前信息加工的方法,研究自然情境中的认知,关注环境对智能的影响。嗣后,情境认知、情境学习与情境化人工智能逐渐形成热潮,继而酿造出第二代认知科学———具身认知。该理论一经诞生旋即颠覆了传统认知心理学的主流观点。在第一代认知科学看来,认知是人“颈部以上”的功能,它把认知比喻为计算机对抽象符号的加工与运算,是运行在大脑这一“硬件”上的“软件”或“程序”。[15]而具身认知理论则认为,认知是具身的、情境的、发展的与动力学的;心智是嵌入大脑的,大脑是嵌入身体的,身体是嵌入环境的,环境是认知系统的一部分。因此,身体、认知与环境是三位一体的。即,认知是被身体及其活动方式塑造的结果,它不是一个运行在身体“硬件”上的“心智程序软件”,而是与身体和环境共同构成了一个相互作用的统一体。[16]
不可否认,具身认知消解了传统上“身心对立”的思维方式,建构了“身心一体”的认知话语。它抓住传统认知“对身体的忽视”这一缺陷,在两极对立的观点之间开辟了一条中间道路。而就在此前,多媒体学习的认知理论还坚称,认知即是对信息加工的过程,是学习者对诸如以语词与画面形式呈现的材料的选择、排列与组合,至于诸如记忆、分类与推理等高阶认知活动的展开,则更多地依赖抽象的言语符号。[17]时至当下,学界已然认识到,认知活动并非纯然的信息加工过程,其表征和实操受身体影响并植根于实时的情境之中。因此,应当把具身认知引入数字化学习研究论域,以跳脱传统认知科学形成的思维羁绊,建构一种身体觉知与环境交互的认知图景,推动人工智能时代课程知识习得的“具身化”进程。笔者以为,时下微课程之所以备受青睐,除了其具有主题精微、短小精湛、内容可视、易于更新等特点之外,从更深刻的意义上讲,还因为它所营造的学习环境符应了具身认知的旨趣,为学习者以身心一体的方式进行认知提供了理论支撑与实践空间。具体来说,微课程在身体、认知与环境两两交互方面推动了知识习得的“具身化”:(
1)在身体—认知的维度上,微课程的知识教学是身心合一、深度卷入的“具身化”认知。如前所述,我们的身体、认知与所处的环境是不可分离的,学习是身心在场的认知过程,它在具体的认知情境中发生,主体对知识的理解以“体悟”的方式获得。众所周知,微课程的知识教学突破了传统上线性的时空架构,已把课堂拓展到校园以外的空间,甚至迁移到了虚拟的网络世界。也正是基于教学时空的边界延展与课程实施的流程再造,学生的感官、心智、大脑、身体以及认知方式获得了自由与解放。在微课程所携载的知识点视频、拓展性链接、个性化推送以及即时性评测等数字化学习环节,学生的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系统得以综合运用,他们以深度卷入的状态体验声、光、电、网等所营造的学习环境,深度参与到对知识的感知、推理、确证与迁移等信息加工过程之中。借助资源的丰富性、内容的可视化与感官的交互性,微课程洞开了多官能协同的认知通道,确证了学习是人身心卷入的认知活动。
(2)在认知—环境的维度上,微课程的知识教学促进了认知过程与学习环境的相互交融。不可否认,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传统的课堂环境正在接受新技术的改造,微课程所形构的课堂已不只是局限在校园围墙之内的物理场所,而是正日趋变成一个由师生、技术、资源、环境等构成的人本化、智能化与泛在性的学习空间。在此空间中,作为身心一体的学习者是认知主体,信息技术、数字技术、媒介技术以及它们创造的流媒体、富媒体、超媒体构成了数字化的学习环境。在具身观的视界里,除了基于认知主体的身体、大脑、器官而生发的生理、心理与精神上的内部环境之外,外部实体性的物理环境与智能化的虚拟环境亦可视为主体认知过程的组成部分。认知不再是身体感受器简单地接受环境刺激后,大脑对这些信号进行编码处理从而如实地映照出外界环境,而是业已嵌入到环境之中的身体主动去建构认知。在这里,环境的影响与认知的建构同等重要,认知与环境在相互作用的过程中紧密地融为了一体。以此观之,微课程拓展并整合了传统认知过程所赖以进行的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实体环境与虚拟环境,推动了信息化条件下认知过程与认知环境的相互影响与彼此塑造。
(3)在身体—环境的维度上,微课程的知识习得趋于把人的神经系统与电子媒介“合并”。诚如前述,认知是身心一体的,身体是嵌入环境的,环境本身也是认知的对象。因此,人的心智、头脑、身体与世界是不可分离且合作共变的。对此,新近的神经科学与媒介技术研究结果表明:我们的生物神经系统与电子媒介具有合并的可能。[18]而事实上,这一思想在西方传播学宗师麦克卢汉(EricMcluhan)那里早已萌发,对麦氏关于“媒介是人类器官的延伸”的论断,人们过去仅仅将之理解为媒介的超强功能,即便在数字化学习的当下,也仅仅把网络视作为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学习方式提供了可能的媒介,而未能更进一步跳脱媒介功能论的认识藩篱。回过头看,虽然麦克卢汉的论述止步于“电子媒介是人的生物神经系统的体外延伸”,但这一观点与具身认知及其所借助的媒体技术分享了共同的观念与主题,这为我们理解微课程在数字化学习中所扮演的角色提供了启示:就当下的微课程研究而言,学习者的认知风格、个体需要、学习时空、情感情绪等个性化因素,已日渐成为微课程设计的技术变量,以便为认知主体定制更加灵活、更具人性、更加开放的智能化学习环境。循此理路,实现人的生物神经系统与电子媒介技术高效交互,创生一种具身的、系统的、智慧的数字化学习新世界,无疑是信息技术、神经系统与课程教学深度融合的未来趋势。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前述对微课程视界中知识样态的时代表征所作的理论探讨,勾勒了我们对信息技术与学科教学融合的发展愿景:微课程以“网络化”“可视化”“具身化”的方式来表征知识,势必深刻变革长期以来僵滞固化的教与学的关系、内容、方式与效能,并终将打破传统上不可复演、不可观测、不可体验的知识观念。然而,由此衍生的一系列问题又接踵而至:微课程视界中的知识演化是一蹴而就的吗?现代技术仅仅是一种认知工具,还是它本身就是知识的物质体现?引发微课程知识样态向此嬗变的动因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有待我们慎思追问并接续解答的基本问题。
参考文献:
[1]戴维?温伯格.知识的边界[M].胡泳,高美,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4.
[2]郑小军,张霞.微课的六点质疑及回应[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4(2):50-51.
[3]余宏亮.微课程意涵三重判读[J].课程?教材?教法,2015(5):35-42.
[4]梁乐明,等.微课程设计模式研究———基于国内外微课程的对比分析[J].开放教育研究,2013(1):65-73.
[5]孙艳超.真是一图胜千言吗?———兼评《计算机、可视化与历史学:新技术将如何改变我们对过去的理解》[J].现代教育技术,2010(8):150.
[6]瞿葆奎.教育学文集?教学(中册)[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185.
[7]W.J.T.米歇尔.图像理论[M].陈永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2.
[8]赵慧臣.知识可视化的视觉表征研究[D].南京:南京师范大学,2010.
[9]王淑芬.网络技术下知识可视化的课堂教学范式重建[J].课程?教材?教法,2014(7):43-45.[
10]崔允漷.有效教学[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6.
[11]John Dewey.Democracyand Education:AnIntroduc- tiontothePhilosophyofEducation[M].New York: Thefreepress,1916:161.
[12]Wang Minhong,WuBian,Kinshuk,ChenNianshing, SpectorJ Michael.Connecting Problem-Solving and Knowledge-Construction Processesina Visualization- basedLearing Environment[J].Computers & Educa- tion,2013(10):293-306.
[13]梅洛?庞蒂.知觉现象学[M].姜志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1-15.
[14]Varela,F.,Thompson,E.,Rosch,E.TheEmbodied Mind.Cambridge,MA:MITPress.1991:173.
[15]叶浩生.具身认知:认知心理学新取向[J].心理科学进展,2010(5):705-710.
[16]Shapiro,L.The Embodied Cognition Research Pro- gramme[J].PhilosophyCompass,2007,2(2):338-346.
[17]郑旭东,等.多媒体学习研究的未来:基础、挑战与趋势[J].现代远程教育研究,2013(6):21.
[18]QingLi,BruceClarkandIan Winchester.Instructional designandtechnologygroundedinEnactivism A para- digmshift? [J].BritishJournalofEducationalTech- nology,2010,3(41):403-419.